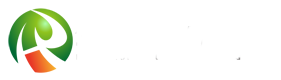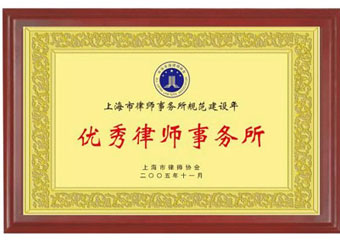條文內容
第三百二十八條 盜掘具有歷史、藝術、科學價值的古文化遺址、古墓葬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并處;情節較輕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并處罰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并處罰金或者:
(一)盜掘確定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和省級文物保護單位的古文化遺址、古墓葬的;
(二)盜掘古文化遺址、古墓葬集團的首要分子;
(三)多次盜掘古文化遺址、古墓葬的;
(四)盜掘占文化遺址、古墓葬,并盜竊珍貴文物或者造成珍貴文物嚴重破壞的。
盜掘國家保護的具有科學價值的古人類化石和古脊椎動物化石的,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
罪名精析
釋義闡明
本條是關于盜掘具有歷史、藝術、科學價值的古文化遺址、古墓葬,盜掘國家保護的具有科學價值的古人類化石和古脊椎動物化石的犯罪及其刑事處罰的規定。共分為兩款。
本條第1款是關于盜掘古文化遺址、古墓葬的犯罪及其刑事處罰的規定。本條中的“盜掘”,是指以出賣或者非法占有為目的,私自秘密發掘古文化遺址和古墓葬的行為。“古文化遺址”,是指在人類歷史發展中由古代人類創造并留下的表明其文化發展水平的地區,如周口店。“古墓葬”,是指古代(一般指清代以前,包括清代)人類將逝者及其生前遺物按一定方式放置于特定場所并建造的固定設施。辛亥革命以后,與著名歷史事件有關的名人墓葬、遺址和紀念地,也視同古墓葬、古遺址,受國家保護。
本條對盜掘古文化遺址、古墓葬的犯罪行為規定了三檔刑罰。其中,對實施了盜掘具有歷史、藝術、科學價值的古文化遺址、古墓葬行為的,處3年以上l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對于情節較輕的,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罰金。根據近年來打擊盜掘古文化遺址、古墓葬犯罪的實際情況,本條具體規定了適用l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刑罰的四種情形:
1.“盜掘確定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和省級文物保護單位的古文化遺址、古墓葬的”。這里的“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有兩種:一種是國家文物行政部門在各級文物保護單位中,直接指定并報國務院核定公布的單位;另一種是國家文物行政部門在各級文物保護單位中,選擇出來的具有重大歷史、藝術、科學價值并報國務院核定公布的單位。“省級文物保護單位”是指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核定并報國務院備案的文物保護單位。被確定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和省級文物保護單位的古文化遺址、古墓葬,在科學、歷史、藝術等方面的價值是極高的。文物保護法規定,一切考古發掘工作,必須履行報批手續;從事考古發掘的單位,應當經國務院文物行政部門批準。地下埋藏的文物,任何單位或者個人都不得私自發掘。從事考古發掘的單位為了科學研究進行考古發掘,應當提出發掘計劃,報國務院文物行政部門批準;對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考古發掘計劃,應當經國務院文物行政部門審核后報國務院批準。國務院文物行政部門在批準或者審核前,應當征求社會科學研究機構及其他科研機構和有關專家的意見。上述古文化遺址、古墓葬一旦被盜掘,對國家文化財產造成的損失根本無法彌補,不處以重刑不具有威懾力。
2.“盜掘古文化遺址、古墓葬集團的首要分子”。“首要分子”是指在盜掘古文化遺址、古墓葬的集團犯罪活動中起組織、策劃、指揮作用的犯罪分子。近年來,盜掘古文化遺址、古墓葬犯罪活動越來越集團化、職業化、高智能和高技術化,而且往往是盜掘與倒賣聯合在一起,形成網絡。因此,嚴厲打擊盜掘古文化遺址、古墓葬犯罪的首要分子很有必要。
3.“多次盜掘古文化遺址、古墓葬的”。“多次”一般是指三次以上。該項規定主要針對的是盜掘古文化遺址、古墓葬的慣犯。
4.“盜掘古文化遺址、古墓葬,并盜竊珍貴文物或者造成珍貴文物嚴重破壞的”。“盜竊珍貴文物”是指在盜掘中將珍貴文物據為己有的行為。這里將盜竊的文物限于“珍貴文物”,盜竊一般文物的不屬于本項情節。盜掘行為與珍貴文物破壞的情況關系緊密,而且盜掘古文化遺址、古墓葬的目的,往往就是為了盜竊珍貴文物。所以,本款將上述行為規定為盜掘古文化遺址、古墓葬罪處重刑的情節。
本條第2款是關于盜掘國家保護的具有科學價值的古人類化石和古脊椎動物化石的犯罪及其刑事處罰的規定。化石是過去生物的遺骸或遺留下來的印跡,是指保存在各地質時期巖層中生物的遺骸和遺跡。“古脊椎動物化石”是指石化的古脊椎動物的遺骸或遺跡(主要指一萬年以前埋藏地下的古爬行動物、哺乳動物和魚類化石等)。“古人類化石”是指石化的古人類的遺骸或遺跡(主要指距今一萬年前的直立人,早期、晚期智人的遺骸,如牙齒、頭蓋骨、骨骼)。這些古人類化石和占脊椎動物化石對研究人類發展史和自然科學具有重要意義。文物保護法規定對其保護適用文物保護的規定。“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是指盜掘國家保護的具有科學價值的古人類化石和古脊椎動物化石的,依照本條第1款規定的三檔刑罰進行處罰。
構成要件
一、概念及其構成
盜掘古文化遺址、古墓葬罪,是指盜掘具有歷史、藝術、文化、科學價值的古文化遺址、古墓葬以及具有科學價值的古人類化石和古脊椎動物化石的行為。
(一)客體要件
本罪侵犯的客體是國家對古文化遺址、古墓葬的管理制度。我國具有豐富的文物,其中相當部分是舉世公認的珍寶。盜掘古文化遺址、古墓葬的行為不但造成文物的嚴重流失,而且使許多文物因失去保護而喪失其歷史、藝術、科學價值,有的甚至造成文物的直接毀壞,因而這種行為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
盜掘古文化遺址、古墓葬罪的犯罪對象限于具有歷史、藝術、科學價值的古文化遺址、古墓葬,而不包括所有的文物。所謂“文物”,是指一切具有歷史、藝術、科學價值的文獻和實物,根據《文物保護法》的規定,我國的文物具體包括:具有歷史、藝術、科學價值的古文化遺址、古墓葬、古建筑、古窟寺和石刻;與重大歷史事件、革命運動和著名人物有關的,具有重要教育意義和史料價值的建筑物遺址、紀念物;歷史上各時代珍貴的藝術品、工藝美術品;重要革命文獻資料以及具有歷史、藝術、科學價值的手稿、古舊圖書資料等;反映歷史上各時代、各民族社會制度、社會生產、社會生活的代表性實物等;所謂“古文化遺址、古墓葬”,根據1987年11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盜竊、盜掘、非法經營和走私文物的案件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釋》的規定,具體指清代和清代以前的具有歷史、藝術、科學價值的古文化遺址、古墓葬及辛亥革命以后與著名歷史事件有關的名人墓葬遺址和紀念地。其中古文化遺址包括石窟、地下城、古建筑等,古墓葬包括皇帝陵墓、革命烈士墓等。如果行為侵犯的不是上述古文化遺址、古墓葬,而是其他有關文物的,不構成本罪。
(二)客觀要件
本罪在客觀方面表現為盜掘古文化遺址、古墓葬的行為,所謂盜掘,既不同于單純的盜竊行為,也不同于對文物的破壞行為,它是指未經國家文化主管部門批準的私自掘取行為,其行為方式有的是秘密的,有的是明火執仗公開進行掘取;有的是單個人實施,有的則多人合伙甚至聚眾實施。
本罪屬于行為犯而不是結果犯,只要行為人實施了盜掘古文化遺址、古墓葬的行為就已構成本罪,至于是否造成使古文化遺址、古墓葬受到嚴重破壞的結果,只對確定本罪適用的法定刑有意義。在實踐中,雖然盜掘古文化遺址、古墓葬行為一般都會對古文化遺址、古墓葬造成嚴重破壞,但也有些行為確未使古文化遺址、古墓葬受到嚴重破壞,對此不能認為不構成犯罪或只構成犯罪預備或。
(三)主體要件
本罪的主體是一般主體。單位能否構成本罪主體,法律無明文規定,我們認為,根據其他有關對的法律規定來理解,如果本罪是在單位名義組織策劃下實施的,可以對單位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追究刑事責任,而不宜對單位直接追究刑事責任。
(四)主觀要件
本罪在主觀方面表現為故意,而且一般具有非法占有古文化遺址、古墓葬中文物的目的。本罪能否由間接故意構成,理論上有肯定與否定兩種截然對立的觀點。我們認為只要行為人的盜掘行為出于故意,其對盜竊的對象是否屬于古文化遺址、古墓葬的文物即使是不確定的,也可以構成本罪。因而本罪可以由間接故意構成。
認定要義
一、罪與非罪的界限
可以從兩個方面對其加以區分:
(1)看其掘取古文化遺址、古墓葬行為是故意實施的還是過失實施的,如果屬于過失行為則不構成犯罪。
(2)看其掘取古文化遺址、古墓葬行為是否經過了國家文化主管部門的批準,如果屬于經過批準的行為,即便在掘取過程中造成古文化遺址、古墓葬毀壞的,一般也不構成犯罪,如果情節嚴重的可以按等其他罪論處。
二、本罪與的界限
1.侵犯的客體不同。盜掘古文化遺址、古墓葬罪侵犯的客體是復雜客體,即國家對古文化遺址、古墓葬的管理制度和國家的財產所有權;而盜竊罪侵犯的是單一客體,即公私財產所有權。前者侵犯的對象是古文化遺址、古墓葬,是不可再生物,一般是不能以金額計算的,一旦遭到破壞,損失無法挽回;后者侵犯的對象是一般的公私財物。
2.客觀表現不同。前者表現為違反文物保護法規,未經國家文化主管部門批準,私自挖掘古遺址、古墓葬的行為,其行為方式可以是秘密的,也可以是公開的,而且不論是否竊得文物,只要實施了盜掘行為,就構成本罪。后者則表現為秘密竊取公私財物,構成犯罪必須以盜竊數額較大為前提,如果未竊取到財物,就是盜竊未遂。
三、本罪與故意損毀文物、故意損毀名勝古跡罪的界限
1.犯罪對象不同。盜掘古文化遺址、古墓葬罪限于古文化遺址、古墓葬;故意損毀文物、名勝古跡罪對象則限于珍貴文物、名勝古跡。
2.在客觀方面,盜竊古文化遺址、古墓葬罪表現為私自掘取的行為,其行為方式多為秘密的;故意損毀文物、名勝古跡罪則表現為損毀行為,其具體表現形式多種多樣,包括搗毀、損壞、污損、拆除、挖掘、焚燒等行為。
3.在主觀方面,盜掘古文化遺址、古墓葬罪一般具有非法占有古文化遺址、古墓葬中文物的目的,故意損毀珍貴文物、名勝古跡罪則只是出于損毀的故意,其動機可能多種多樣,但并無對文物非法占有的目的。
量刑標準
依照《》第328條第1款的規定,犯盜掘古文化遺址、古墓葬罪的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情節較輕的,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罰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
1.盜掘確定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和省級文物保護單位的古文化遺址、古墓葬的;
2.盜掘古文化遺址、古墓葬集團的首要分子;
3.多次盜掘古文化遺址、古墓葬的;
4.盜掘古文化遺址古墓葬,并盜竊珍貴文物或者造成珍貴文物嚴重破壞的。
對于可以判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的四種情形:
1.確定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和省級文物護單位的古文化遺址、古墓葬具有極高的歷史、藝術、科學價值,應受到特別重點的保護。被盜掘竊取的文物等級及其歷史、藝術、科學價值應請專家鑒定;
2.盜掘古文化遺址、古墓葬集團的首要分子,是指在盜掘古文化遺址古墓葬的犯罪集團中起組織、策劃、指揮作用的犯罪分子。對首要分子應作為打擊重點,嚴厲懲處;
3.“多次”盜掘古文化遺址、古墓葬,是指三次以上。
解釋性文件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妨害文物管理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2016年1月1日 法釋〔2015〕23號)
第八條 刑法第三百二十八條第一款規定的“古文化遺址、古墓葬”包括水下古文化遺址、古墓葬。“古文化遺址、古墓葬”不以公布為不可移動文物的古文化遺址、古墓葬為限。
實施盜掘行為,已損害古文化遺址、古墓葬的歷史、藝術、科學價值的,應當認定為盜掘古文化遺址、古墓葬罪既遂。
采用破壞性手段盜竊古文化遺址、古墓葬以外的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壁畫、近代現代重要史跡和代表性建筑等其他不可移動文物的,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條的規定,以盜竊罪追究刑事責任。
第十一條 單位實施走私文物、倒賣文物等行為,構成犯罪的,依照本解釋規定的相應自然人犯罪的定罪量刑標準,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定罪處罰,并對單位判處罰金。
公司、企業、事業單位、機關、團體等單位實施盜竊文物,故意損毀文物、名勝古跡,過失損毀文物,盜掘古文化遺址、古墓葬等行為的,依照本解釋規定的相應定罪量刑標準,追究組織者、策劃者、實施者的刑事責任。
第十三條 案件涉及不同等級的文物的,按照高級別文物的量刑幅度量刑;有多件同級文物的,五件同級文物視為一件高一級文物,但是價值明顯不相當的除外。
第十四條 依照文物價值定罪量刑的,根據涉案文物的有效價格證明認定文物價值;無有效價格證明,或者根據價格證明認定明顯不合理的,根據銷贓數額認定,或者結合本解釋第十五條規定的鑒定意見、報告認定。
第十五條 在行為人實施有關行為前,文物行政部門已對涉案文物及其等級作出認定的,可以直接對有關案件事實作出認定。
對案件涉及的有關文物鑒定、價值認定等專門性問題難以確定的,由司法鑒定機構出具鑒定意見,或者由國務院文物行政部門指定的機構出具報告。其中,對于文物價值,也可以由有關價格認證機構作出價格認證并出具報告。
第十六條 實施本解釋第一條、第二條、第六條至第九條規定的行為,雖已達到應當追究刑事責任的標準,但行為人系初犯,積極退回或者協助追回文物,未造成文物損毀,并確有悔罪表現的,可以認定為犯罪情節輕微,不起訴或者免予刑事處罰。
實施本解釋第三條至第五條規定的行為,雖已達到應當追究刑事責任的標準,但行為人系初犯,積極賠償損失,并確有悔罪表現的,可以認定為犯罪情節輕微,不起訴或者免予刑事處罰。
第十七條 走私、盜竊、損毀、倒賣、盜掘或者非法轉讓具有科學價值的古脊椎動物化石、古人類化石的,依照刑法和本解釋的有關規定定罪量刑。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關于盜掘古文化遺址罪適用法律問題的研究意見》
【延伸閱讀】《關于盜掘古文化遺址罪適用法律問題的研究意見》的理解與適用
有關部門就盜掘古文化遺址罪適用法律問題征求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意見。
經認真研究,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認為,盜掘古文化遺址罪的犯罪對象為古文化遺址的保護范圍,不包括建設控制地帶。行為人為盜掘古文化遺址,但因對古文化遺址保護范圍與建設控制地帶的界限認識不清,而在建設控制地帶進行盜掘的,構成盜掘古文化遺址罪(未遂)。
證據規格
盜掘古文化遺址、古墓葬罪
一、主體方面的證據
(一)證明行為人刑事責任年齡、身份等自然情況的證據
包括身份證明、戶籍證明、任職證明、工作經歷證明、特定職責證明等,主要是證明行為人的姓名(曾用名)、性別、出生年月日、民族、籍貫、出生地、職業(或職務)、住所地(或居所地)等證據材料,如戶口簿、居民身份證、工作證、出生證、專業或技術等級證、干部履歷表、職工登記表、護照等。
對于戶籍、出生證等材料內容不實的,應提供其他證據材料。外國人犯罪的案件,應有護照等身份證明材料。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犯罪的案件,應注明身份,并附身份證明材料。
(二)證明行為人的證據。證明行為人對自己的行為是否具有辨認能力與控制能力,如是否屬于間歇性精神病人、尚未完全喪失辨認或者控制自己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的證明材料。
二、主觀方面的證據
證明行為人故意的證據:
(一)證明行為人明知的證據:證明行為人明知自己的行為會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
(二)證明直接故意的證據:證明行為人希望危害結果發生;
(三)目的:非法占有文物。
三、客觀方面的證據
證明行為人盜掘古文化遺址、古墓葬犯罪行為的證據。
具體證據包括:
(一)證明行為人盜掘確定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古文化遺址、古墓葬行為的證據;
(二)證明行為人盜掘確定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的古文化遺址、古墓葬行為的證據;
(三)證明行為人盜掘古文化遺址、古墓葬集團首要分子的證據;
(四)證明行為人多次盜掘古文化遺址、古墓葬行為的證據;
(五)證明行為人“盜掘”同時,盜竊珍貴文物行為的證據:
1.一級文物;
2.二級文物;
3.三級文物。
(六)證明行為人“盜掘”同時,盜竊珍貴文物行為的證據:
1.一級文物;
2.二級文物;
3.三級文物。
(七)證明行為人盜掘古文化遺址、古墓葬行為的證據;
(八)證明行為人盜掘古文化遺址、古墓葬情節較輕行為的證據。
四、量刑方面的證據
(一)法定量刑情節證據
1.事實情節:
(1)情節嚴重;
(2)其他。
2.法定從重情節:
3.法定從輕減輕情節:
(1)可以從輕;
(2)可以從輕或減輕;
(3)應當從輕或者減輕。
4.法定從輕減輕免除情節:
(1)可以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
(2)應當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
5.法定減輕免除情節:
(1)可以減輕或者免除處罰;
(2)應當減輕或者免除處罰;
(3)可以免除處罰。
(二)酌定量刑情節證據。
1.犯罪手段:
(1)秘密盜掘;
(2)秘密竊取。
2.犯罪對象;
3.危害結果;
4.動機;
5.平時表現;
6.認罪態度;
7.是否有前科;
8.其他證據。
案例精選
《刑事審判參考》第266號案例 李生躍盜掘古文化遺址案
【摘要】
盜割石窟寺內壁刻頭像的行為應如何定罪?
刑法第三百二十八條中的“古文化遺址”是否包括石窟寺等其他不可移動的文物在內,是本案爭議的焦點。由此對本案的定性產生了三種觀點。
李生躍盜掘古文化遺址案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李生躍,男,生于1969年1月20日,漢族,小學文化,農民。2001年3月8日因涉嫌犯
盜竊罪
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12日被逮捕,12月20日被決定勞動教養三年。2002年10月28日因涉嫌犯盜掘古文化遺址罪被刑事拘留,同年11月1日被逮捕。
四川省廣元市人民檢察院以被告人李生躍犯盜掘古文化遺址罪向廣元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公訴。
被告人李生躍及其辯護人辯稱,其盜割石窟寺內壁刻頭像的行為不構成盜掘古文化遺址罪。
廣元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公開審理查明:2001年1月12日晚,被告人李生躍攜帶扁鉆、手錘等作案工具,翻圍墻進入廣元市市中區盤龍鎮境內的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觀音巖摩崖造像(石窟寺)保護區內,盜鑿走該保護區內摩崖造像頭像2尊,銷贓得款800元。同年2月21日晚,李生躍再次竄入觀音巖保護區內,采用同樣的方法鑿取頭像6尊。同年3月6日李在銷贓時被公安機關當場抓獲。所獲贓物共8尊頭像已被收繳,并歸還廣元市市中區文物管理所。
廣元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后認為,被告人李生躍盜掘具有歷史、藝術、科學價值的省級文物保護單位的唐代觀音巖摩崖造像頭像八尊,其行為已構成盜掘古文化遺址罪。公訴機關指控罪名成立,予以采納。李生躍及其辯護人在庭審中辯解及辯護該行為不構成盜掘古文化遺址罪,經查,《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雖把石窟寺與古文化遺址并列,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二十八條所規定的犯罪對象則是古文化遺址、古墓葬,沒有明確列出石窟寺,但這并不說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二十八條排除了對石窟寺的保護。從立法本意上講,《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二十八條所稱的古文化遺址應包括石窟寺等其他不可移動的文物在內。李生躍及其辯護人的上述辯解、辯護意見于法無據,不予支持。鑒于李生躍歸案后,承認犯罪事實,認罪態度好,有悔罪表現,可酌定予以從輕處罰。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二十八條第一款(一)項、第五十二條、第六十四條的規定,于2003年9月4日判決如下:
1.被告人李生躍犯盜掘古文化遺址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年,并處罰金10,000元。
2.作案工具手錘一把、扁鉆三根、背簍一個,尼龍繩一根、編織帶一個,予以沒收。
一審宣判后,被告人李生躍不服,以原判定性不準,適用法律錯誤為由,提出上訴。其辯護人亦提出相同的辯護意見。
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廣元市觀音巖被盜的佛造像頭像系省級文物保護單位廣元市觀音巖摩崖造像的重要組成部分,其造型生動優美,是我國古代勞動人民智慧的結晶,具有較高的歷史、藝術、科學價值。上訴人李生躍為了牟取非法利益,故意盜掘廣元市觀音巖摩崖佛造像頭像,其行為破壞了國家文物的整體完整性和文物價值,對省級文物保護單位廣元市觀音巖摩崖佛造像造成了不可彌補的損失,已構成盜掘古文化遺址罪。《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二十八條中的“古文化遺址”,應當包括石窟、地下城、古建筑等。上訴人李生躍及其辯護人以原判定性不準,適用法律錯誤的上訴理由及其辯護意見不能成立,不予采納。原判認定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適用法律正確,量刑適當,審判程序合法。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百八十九條第(一)項的規定,于2003年10月29日裁定如下: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二、主要問題
盜割石窟寺內壁刻頭像的行為應如何定罪?
刑法第三百二十八條中的“古文化遺址”是否包括石窟寺等其他不可移動的文物在內,是本案爭議的焦點。由此對本案的定性產生了三種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考慮立法意旨,刑法第三百二十八條中的“古文化遺址”應當包括石窟寺等其他不可移動的文物在內,李生躍為牟取非法利益,故意盜掘具有較高歷史、藝術、科學價值的省級文物保護單位石窟寺內壁刻頭像,其行為已構成盜掘古文化遺址罪。
第二種觀點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第二條第一項規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下列文物受國家保護:(一)具有歷史、藝術、科學價值的古文化遺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和石刻、壁畫。”第三條第一款規定:“古文化遺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壁畫、近現代重要史跡和代表性建筑等不可移動文物,根據它們的歷史、藝術、科學價值可以分別確定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市縣級文物保護單位。”據此可見,古文化遺址不應包括石窟寺在內。其次,所謂“盜掘”,本意應當是指私自開挖,挖掘的行為,開挖,挖掘的對象主要是地下埋藏的文物。本案被告人李生躍盜鑿省級文物保護單位石窟寺內壁刻頭像的行為,并不屬于嚴格意義上的“掘”。故本案不宜定盜掘古文化遺址罪。由于本案被告人李生躍盜鑿省級文物保護單位石窟寺內壁刻頭像的行為客觀上已造成省級文物保護單位的部分毀損,故可定故意損毀文物罪。
第三種意見認為,故意損毀文物罪的主觀方面只能是損毀的故意,本案被告人李生躍盜鑿省級文物保護單位石窟寺內的壁刻頭像,是以非法占有,出售牟利為目的,故其行為不構成故意損毀文物罪,而應定盜竊(文物)罪。
三、裁判理由
(一)對刑法第三百二十八條中的“古文化遺址”,應作廣義上的理解,其應當包括石窟寺、石刻、古建筑、地下城等。
《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以下簡稱文物保護法)將“古文化遺址”與“石窟寺”并列表述。其中所稱的“古文化遺址”,是指除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壁畫、近現代重要史跡和代表性建筑等之外的不可移動文物的一個種類,是不可移動文物種類上的專業細分,故其含義相對較窄。主要是指古代的建筑廢墟以及古人類社會活動的所遺留下來的遺跡。石窟寺,簡稱石窟,則主要指是古代一種在崖體開鑿而成,內有佛像或佛教故事的壁畫、石刻等的佛教建筑。原則而言,在刑事立法中使用有關的專業術語,以及在刑事司法中對刑法條文內有關專業術語的解釋,都應當盡量與相關部門法的專業用語保持一致,這是保持各部門法律整體內在統一性的需要。但考慮到刑法規范與相關行政管理法規范所要規制的目的不同,有時二者雖使用同一術語,但在含義上卻有所不同,或者說需要作出不同的解釋,這也是常見的現象。比如,刑法中所使用的偽劣商品就不能等同于產品質量管理法中所稱的偽劣商品,前者是狹義的,后者是廣義的。“古文化遺址”也有廣義、狹義之分。廣義的“古文化遺址”可以用來泛指一切古代文化活動的遺跡或遺物,也就是說,在不可移動文物中,除近現代重要史跡和代表性建筑因不屬于古文化范疇,古墓葬因刑法另由單獨規定外,其他如石窟寺、石刻、古建筑、地下城等,都可以視為是廣義的“古文化遺址”。文物保護法使用的是狹義上的“古文化遺址”,目的是為了盡可能的列舉不可移動文物所包含的種類,形態,明確文物保護范圍。而對于刑法第三百二十八條所稱的“古文化遺址”,其含義應當是廣義的,或者說有必要作與文物保護法所不同的廣義上的理解。也只有如此解釋,才能將石窟寺、石刻、古建筑、地下城等不可移動文物(文物保護單位)納入刑法的保護范圍,才更加合乎刑事立法的意旨。
(二)所謂“盜掘”既包括私自開挖,挖掘地下埋藏的文物的行為,也應包括將不可移動文物的一部分從其整體中挖掘,鑿割下來的行為。
“掘”乃挖掘之意,將完全于地下埋藏的文物如古墓葬開挖出來,是“掘”;將半埋于地下(一部分在地下,一部分在地上)的不可移動文物挖出也是“掘”。此外,那種將不可移動文物的一部分從其整體中挖掘,鑿割下來的行為,同樣也是“掘”。可見,“掘”既包括朝地下垂直式的挖掘,也包括水平面上的挖掘。如本案被告人李生躍鑿挖附著于山體表面上的壁刻頭像的行為,就是一種水平面上的挖掘。那種將“掘”理解為僅指向下開挖地下文物的行為,顯然是機械、片面的。
綜上,我們認為,本案被告人李生躍以占有出售為目的,盜鑿已被確定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的石窟寺內壁刻頭像的行為,符合盜掘古文化遺址罪的特征,對其應以盜掘古文化遺址罪定罪,且得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并處罰金或沒收財產的法定刑幅度內處斷刑罰。被告人李生躍在實施上述行為時,雖主觀上具有損毀省級文物保護單位文物的放任故意,客觀上已造成省級文物保護單位文物部分毀損的后果,但其直接故意并非損毀文物,因此,不能定故意損毀文物罪。即便說李生躍的上述行為系一行為同時觸犯兩罪名,由于盜掘古文化遺址罪的法定刑重于故意損毀文物罪,根據擇一重處斷的原則,本案也應以盜掘古文化遺址罪定罪。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本案也不能定盜竊(文物)罪。盜竊(文物)罪的對象一般應當是可移動文物。根據文物保護法第三條第二款規定,歷史上各時代重要實物、藝術晶、文獻、手稿、圖書資料、代表性實物等可移動文物,分為珍貴文物和一般文物,珍貴文物又分為一級文物、二級文物、三級文物。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盜竊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也是根據行為人所盜竊的文物是一般文物,還是珍貴文物,屬于何種等級的珍貴文物以及盜得的文物數量來確定相關的處刑標準的。針對不可移動文物(文物保護單位)的犯罪行為,其主要形式是盜掘和損毀,是否屬于國家或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是其定罪量刑的重要依據之一。不可移動文物和可移動文物是文物的基本分類之一,前者作為一個完整的整體,具有不可分割性,實踐中很難整體被盜走,而對其任何一個部分進行涂、畫、刻、鑿、割等行為,都是對整體文物價值的破壞,應按其行為性質分別確定為是損毀還是盜掘。將不可移動文物的一部分鑿割下來盜走的行為,屬于盜掘,被盜掘走的部分,有的可能再被看做是一個獨立的文物(從辦案角度看,需要事后另作文物鑒定),有的也可能構不成一個獨立的文物或者文物價值完全喪失。而盜竊可移動文物的行為一般是秘密徑直竊走,無需針對文物本身采取如挖、掘、鑿、敲、鉆等行為方式。本案的犯罪對象是省級文物保護單位石窟寺,屬不可移動文物,行為方式是挖掘,不符合盜竊罪的犯罪對象和行為方式特征。此外,本案被盜鑿下來的壁刻頭像,是否具有獨立的文物價值,能否再被看做是一個獨立的文物,也沒有鑒定,若認定為盜竊(文物)罪,在量刑上也將無法適從。且盜掘古文化遺址罪與盜竊(文物)罪法定最高刑一致,將本案認定為盜掘古文物遺址罪,既符合該罪構成和被告人的行為特征,又能體現罪責刑相一致的原則,對被告人處以相應的刑罰。
《刑事審判參考》第485號案例 孫立平等盜掘古墓葬案
【摘要】
如何認定盜掘古墓葬罪中的既遂和多次盜掘?
1.盜掘古墓葬罪屬于以完成一定的行為作為構成犯罪的行為犯,只要被告人有盜掘古墓葬的主觀故意,客觀上實施了一定的盜掘行為,就可認定既遂,這是符合我國刑法第三百二十八條盜掘古墓葬罪的立法精神的。
2.從一般意義上來理解,結合刑法其他罪名對多次認定的慣行標準,可以將3次以上盜掘古墓葬的認定為多次盜掘。針對同一古墓葬的分次挖掘,不能簡單地以多次重復的機械動作和行為作為次數的標準,而應以盜掘不同的古墓葬為標準,否則在間隔時間、參與人員等方面亦很難把握。
孫立平等盜掘古墓葬案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孫立平,男,1967年7月24日出生,小學文化,農民。因涉嫌犯盜掘古墓葬罪于2007年4月29日被逮捕。
被告人劉和平,男,1976年8月11日出生,初中文化,農民。因涉嫌犯盜掘古墓葬罪于2006年12月22日被逮捕。
被告人徐建峰,男,1968年12月14日出生,初中文化,農民。因涉嫌犯盜掘古墓葬罪于2006年12月22日被逮捕。
被告人胡志明,男,1969年11月18日出生,初中文化,農民。因涉嫌犯盜掘古墓葬罪于2007年1月11日被逮捕。
(其他被告人略)
浙江省湖州市人民檢察院以孫立平等11名被告人犯盜掘古墓葬罪向湖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公訴。
湖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公開審理查明:
1.2006年9月,被告人徐建峰、劉和平、胡志明伙同吳傳貴、小義”、小李”、單洪水(均另案處理)在安吉縣高禹鎮小白山工業園區內盜掘一座古墓,竊得黑地朱彩曲折紋奩1件、黑地朱彩云氣紋案1件、黑地朱彩云氣紋盒2件、青銅劍1件、四鳳菱紋銅鏡1件、銅盉1件、黑漆平幾1件、黑漆博局1件、黑漆素面大盤1件、黑漆木梳1件、黑地朱彩云氣卮1件、黑漆古瑟1件、彩繪陶俑2件、彩繪陶盒4件、彩繪陶鼎6件、黑地朱彩云氣紋羽觴9件、漆箭5件、彩繪陶杯3件、彩繪淺盤豆2件、彩繪陶鈁5件、木跪俑1件、站立木俑3件、彩繪陶俑3件、彩繪淺盤豆(缺足)2件、漆劍鞘1件,共計59件文物,其中的黑漆古瑟、黑漆博局在作案過程中被嚴重破壞。后經劉和平聯系,被告人沈偉平在明知上述文物是盜掘所得的情況下,仍以人民幣27萬元的價格予以收購。銷贓后,劉和平分得贓款人民幣39000元,徐建峰分得贓款人民幣38600元,胡志明分得贓款38600元,劉和平用部分贓款購買了牌號為皖p50389豐田汽車一輛。
上述被告人在進行該次盜掘作案的過程中,徐建峰又伙同“小義”、“小李”、單洪水另行從該墓中竊得玉器4塊等物,通過“阿星”(另案處理)予以銷贓,共得贓款48000元。其中,徐建峰分得贓款人民幣13000元。
經鑒定,該墓系春秋戰國時期的木槨墓。上述59件文物中的黑地朱彩曲折紋奩、黑地朱彩云氣紋案、黑地朱彩云氣紋盒、青銅劍系一級文物;四鳳菱紋銅鏡、銅盉、黑漆平幾、黑漆博局、黑漆素面大盤、黑漆木梳、黑地朱彩云氣卮、黑漆古瑟、彩繪陶俑系二級文物;彩繪陶盒、彩繪陶鼎、黑地朱彩云氣紋羽觴、漆箭、彩繪陶杯、彩繪淺盤豆、彩繪陶鈁、木跪俑、站立木俑、彩繪陶俑系三級文物;彩繪淺盤豆(缺足)、漆劍鞘系一般文物。
2.2006年10月,被告人孫立平、劉和平、楊建峰、沈玉龍伙同沈加法、“小金”(均另案處理)等人在安吉縣高禹鎮五福村五福自然村胡來順(另案處理)的自留地上盜掘一古墓,竊得青銅劍一把,后由劉和平聯系銷贓給“老陳”(另案處理)。因之前為掘墓由劉和平墊付5000元給胡來順,故所得贓款6000元中劉和平分得5000元,楊建峰得款1000元。盜墓過程中,楊建峰多次用自己的牌號為浙EC2147柳州五菱汽車運載其他被告人到作案現場。同年11月初,楊建峰、孫立平伙同吳傳貴、吉自成、“阿偉”(均另案處理)對該墓再次盜掘,但未掘得物品。經鑒定,該墓屬于具有重要歷史、藝術、科學價值的古墓葬,系西漢初期的貴族墓。
3.2006年9月,被告人孫立平、楊建峰、沈玉龍、廖阿強、孫立元、周從有伙同沈加法、“老陳”、“小金”在安吉縣溪龍鄉紅廟上山林場朱仁有(另案處理)的茶葉山上盜掘一古墓,但未掘得物品。同年10月,上述9人又伙同朱衛云(另案處理)對該墓再次盜掘,亦未掘得物品。經鑒定,該墓系先秦時代的土墩石室墓,屬于古墓葬。
4.2006年9月,被告人孫立平、楊建峰、沈玉龍、周兆華伙同沈加法、“大刁慶”(另案處理)在安吉縣梅溪鎮石龍村富家隊自然村一竹園內盜掘一墓葬,但未掘得物品。經鑒定,該古墓葬具有一定歷史、藝術、科學價值。
5.2006年6、7月,被告人孫立平、楊建峰、廖阿強伙同沈加法、阿旦”、小林”(均另案處理)在安吉縣梅溪鎮石龍村楊梅嶺山上盜掘一墓,但未掘得物品。經鑒定,該墓系先秦時代的土墩石室墓,屬于古墓葬。另查明,案發后,胡志明主動向公安機關投案,并如實供述犯罪事實;楊建峰主動向公安機關檢舉同案犯以外的其他重大犯罪事實。
綜上,被告人劉和平參與盜掘古墓葬2座,盜得珍貴文物56件、一般文物3件,共分得贓款44000元;被告人徐建峰參與盜掘古墓葬1座,盜得珍貴文物56件、一般文物3件,共分得贓款51600元;被告人胡志明參與盜掘古墓葬1座,盜得珍貴文物56件、一般文物3件,分得贓款38600元;被告人孫立平參與盜掘古墓葬4座,盜得青銅劍1把;被告人楊建峰參與盜掘古墓葬4座,盜得青銅劍1把,分得贓款1000元;被告人沈玉龍參與盜掘古墓葬3座,盜得青銅劍1把;被告人廖阿強參與盜掘古墓葬2座;被告人孫立元參與盜掘古墓葬1座;被告人周從有參與盜掘古墓葬1座;被告人周兆華參與盜掘古墓葬1座;被告人沈偉平收購贓物1次,共收購珍貴文物56件、一般文物3件。
湖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被告人劉和平、徐建峰、胡志明、孫立平、楊建峰、沈玉龍、廖阿強、孫立元、周從有、周兆華交叉結伙,盜掘具有歷史、藝術、科學價值的古墓葬,其行為均已構成盜掘古墓葬罪。其中被告人劉和平、徐建峰、胡志明盜掘古墓葬并盜竊珍貴文物,共同盜掘過程中還造成珍貴文物嚴重破壞;被告人孫立平、楊建峰、沈玉龍均多次盜掘古墓葬。公訴機關指控的各罪名均成立。案發后,被告人胡志明自動投案,并如實供述犯罪事實,系自首,依法應予從輕處罰。為維護國家對文物的管理制度,嚴懲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的犯罪分子,根據各被告人犯罪的事實,犯罪的性質、情節,對社會的危害程度,以及犯罪后的表現,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二十八條第一款、第三百一十二條、第二十五條、第六十五條第一款、第六十七條第一款、第六十八條第一款、第五十六條第一款、第五十二條、第六十四條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處理自首和立功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七條之規定,判決如下:
1.被告人劉和平犯盜掘古墓葬罪,判處無期徒刑,終身,并處罰金三萬元。
2.被告人徐建峰犯盜掘古墓葬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剝奪政治權利五年,并處罰金三萬元。
3.被告人胡志明犯盜掘古墓葬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年,并處罰金三萬元。
4.被告人孫立平犯盜掘古墓葬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年六個月,并處罰金六千元。
(其他被告人略)
一審宣判后,十一名被告人沒有提出上訴,公訴機關亦未抗訴,判決已發生法律效力。
二、主要問題
1.如何認定盜掘古墓葬的既遂、未遂?
2.如何認定被告人盜掘古墓葬的次數?
三、裁判理由
(一)如何認定盜掘古墓葬的既遂、未遂?
本案審理中,對于各被告人的行為構成盜掘古墓葬罪控辯雙方沒有爭議,只是對于既遂、未遂問題,多名辯護人提出未盜得文物的不能按既遂論,被告人有些盜掘古墓葬行為屬于未遂的辯護意見。這涉及如何理解盜掘古墓葬罪既遂標準的問題,對此,我們認為:
盜掘古墓葬罪屬于以完成一定的行為作為構成犯罪的行為犯,只要被告人有盜掘古墓葬的主觀故意,客觀上實施了一定的盜掘行為,就可認定既遂,這是符合我國刑法第三百二十八條盜掘古墓葬罪的立法精神的。該條規定:“盜掘具有歷史、藝術、科學價值的古文化遺址、古墓葬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情節較輕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罰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1.盜掘確定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和省級文物保護單位的古文化遺址、古墓葬的;2.盜掘古文化遺址、古墓葬集團的首要分子;3.多次盜掘古文化遺址、古墓葬的;4.盜掘古文化遺址、古墓葬,并盜竊珍貴文物或者造成珍貴文物嚴重破壞的。”可以看出,立法規定成立該罪并不以實際盜得文物為構成要件,僅要求主觀上為故意,客觀上實施了盜掘具有歷史、藝術、科學價值的古文化遺址、古墓葬的行為即可。這是因為,刑法設置該罪旨在保護在歷史、藝術、科學等方面都具有很高的文物價值的古墓葬及其內部文物,但以目前的科技水平,對多數文物最好的保護方法仍是埋藏在地下,一旦挖掘出土,就可能對其造成不可逆轉的破壞或毀壞,甚至迫使國家不得不對其進行搶救性的挖掘,其損失很可能是無法估量的,更遑論那些非法私自采取破壞性手段的盜掘行為了。為此,出于嚴厲打擊此類犯罪的需要,刑法降低構罪門檻,將其規定為行為犯是符合國家嚴格保護文物政策的。盜掘古墓葬罪作為行為犯,其既遂是以一定行為的實施為標準,但一般來說,盜掘古墓葬行為在實踐中會有一個實行過程,我們不能認為一著手實施即可構成犯罪,應當結合承擔刑事責任所要求行為的社會危害程度進行具體分析,嚴格把握盜掘行為是否達到符合刑法規定的界限,如果盜掘行為剛剛開始,并未觸及墓室或未對該墓葬的歷史、藝術、科學價值造成一定影響的,可以不以犯罪論處。
本案的被告人連續多次對古墓葬進行盜掘,除在小白山、五福村墓中掘得文物外,盜掘其他古墓葬均未掘得物品,但從被告人的行為來看,違反相關國家規定私自挖掘古墓葬,并且分別掘及墓室的主體或側墓,已經對古墓葬造成了不可恢復的破壞,從其行為程度看,不僅已著手犯罪,而且其行為已造成了對古墓葬的破壞結果,嚴重侵犯了國家文物管理秩序,應當說符合刑法第三百二十八條規定的行為要件,應屬既遂,辯護人所提有關辯護意見并無法律和事實依據,應予駁回。
(二)如何認定被告人盜掘古墓葬的次數?
1.何為“多次”盜掘?目前刑法尚無對該問題的明確規定。從司法實務中的通常理解來講,刑法條款中的“多次”一般來講是3次,如《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搶劫、搶奪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中對多次搶劫規定為搶劫3次以上;再如《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盜竊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中規定“對于一年內入戶盜竊或者在公共場所扒竊三次以上的,應當認定為‘多次’盜竊,以盜竊罪定罪處罰”。因此,從一般意義上來理解,結合刑法其他罪名對多次認定的慣行標準,可以將3次以上盜掘古墓葬的認定為多次盜掘。
2.何為刑法意義上的“次”?刑法第三百二十八條第(三)項規定對多次盜掘的最高可處死刑,因此,在對是否構成該情節的考慮上,更要注意嚴格把握。關于這一問題,我們認為,可參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搶劫、搶奪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對于“多次”與“一次”搶劫的認定問題的明確解釋:“對于多次的認定,應以行為人實施的每一次搶劫行為均已構成犯罪為前提,綜合考慮犯罪故意的產生、犯罪行為實施的時間、地點等因素,客觀分析、認定。對于行為人基于一個犯意實施犯罪的,如在同一地點同時對在場的多人實施搶劫的;或基于同一犯意在同一地點實施連續搶劫犯罪的,如在同一地點連續地對途經此地的多人進行搶劫的;或在一次犯罪中對一棟居民樓房中的幾戶居民連續實施入戶搶劫的,一般應認定為一次犯罪。”本案中,被告人基于一個犯罪故意,針對同一古墓葬,分次實施盜掘行為,還是應認定一次犯罪。即對于針對同一古墓葬的分次挖掘,不能簡單地以多次重復的機械動作和行為作為次數的標準,而應以盜掘不同的古墓葬為標準,否則在間隔時間、參與人員等方面亦很難把握。
具體到本案中的第一起盜掘犯罪,根據被告人徐建峰、劉和平、胡志明等人的供述,該起犯罪所得贓物59件文物并非一次盜掘得來,而是在一段時間內,被告人對該古墓葬進行了較長時間的連續盜掘,參照上述司法解釋,從“基于同一犯意”的角度考慮,不宜對被告人在這起犯罪中的每一次盜掘作獨立的刑法評價。因此,對這一問題總的把握原則是,一般來講,對被告人出于同一個犯意針對同一古墓葬連續分次盜掘的,如果每次盜掘間隔時間不長,從罪刑均衡角度出發,不宜認定為“多次”。
《刑事審判參考》第560號案例 卞長軍等盜掘古墓葬案
【摘要】
盜掘古墓葬罪中主觀認知的內容和“盜竊珍貴文物”加重處罰情節的適用。
1.盜掘古墓葬罪要求行為人應當明知所盜掘的是古墓葬,但不要求行為人確切認識到所盜掘古墓葬的歷史、藝術、科學價值。
2.如果盜掘中同時竊取文物,尤其竊取珍貴文物的,將直接導致文物在沒有完善保護措施的情況下出土,往往會進一步造成文物的毀損、流失,這較之單一的盜掘行為危害性更大,應在量刑中加以考慮。
卞長軍等盜掘古墓葬案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卞長軍,男,1969年6月25日出生,農民,因涉嫌犯盜掘古墓葬罪于2007年11月27日被逮捕。
被告人卞長波,男,1980年8月25日出生,農民,因涉嫌犯盜掘古墓葬罪于2007年11月27日被逮捕。
被告人卞長天,男,1982年1月6日出生,農民,因涉嫌犯盜掘古墓葬罪于2007年11月27日被逮捕。
被告人卞云勇,男,1965年2月14日出生,農民,因涉嫌犯盜掘古墓葬罪于2007年11月27日被逮捕。
被告人卞長雙,男,1974年10月8日出生,農民,因涉嫌犯盜掘古墓葬罪于2007年11月27日被逮捕。
被告人衡孝狀,男,1974年6月3日出生,農民,因涉嫌犯盜掘古墓葬罪于2007年11月27日被逮捕。
安徽省滁州市鳳陽縣人民檢察院以被告人卞長軍、卞長波、卞長天、卞云勇、卞長雙、衡孝狀犯盜掘古墓葬罪,向滁州市鳳陽縣人民法院提起公訴。
鳳陽縣人民法院經公開審理查明:
2007年5月22日10時許,被告人卞長軍伙同被告人卞長波、卞長天、卞長雙、卞云勇、衡孝狀持鐵鍬等工具至板橋鎮古城村北側古墓群挖找古錢幣。至晚上10時許,卞長軍等人先后盜掘出青銅編鐘二組14件、青銅鼎2件、青銅豆1件、青銅鑒1件、青銅斧1件、馬銜12件等文物。卞長軍等六人發現盜掘的可能屬于國家保護的文物,在還能繼續挖掘的情況下,決定停止挖掘,隨后向板橋派出所報案,并將挖掘出的文物全部主動上交板橋派出所的公安干警。經鑒定,卞長軍等六名被告人盜掘處系春秋時期的古墓,具有重要的科學、藝術和歷史價值;青銅編鐘一組(9件)為國家一級文物,青銅編鐘一組(5件)為國家二級文物,青銅斧、青銅豆為國家三級文物,青銅鼎、青銅鑒、馬銜(完整)、馬銜(斷)為國家一般文物。
鳳陽縣人民法院認為,被告人卞長軍、卞長波、卞長天、卞云勇、卞長雙、衡孝狀違反國家文物保護法,共同盜掘并盜竊具有歷史、藝術、文化、科學價值的春秋時代的古墓葬,其行為均已構成盜掘古墓葬罪,應依法懲處。鑒于六被告人均是偶犯,主觀惡性較輕,且案發后能夠投案,歸案后如實供認其基本犯罪事實,認罪態度較好,具有悔罪表現,文物保存完好并已全部上交。對六被告人可以減輕處罰。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二十八條第(四)項、第六十七條第一款、第二十五條第一款之規定,判決如下:
1.被告人卞長軍犯盜掘古墓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并處罰金人民幣1萬元;
2.被告人卞長波犯盜掘古墓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并處罰金人民幣1萬元;
3.被告人卞長天犯盜掘古墓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并處罰金人民幣1萬元;
4.被告人卞云勇犯盜掘古墓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并處罰金人民幣1萬元;
5.被告人卞長雙犯盜掘古墓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并處罰金人民幣1萬元;
6.被告人衡孝狀犯盜掘古墓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并處罰金人民幣1萬元。
一審宣判后,被告人卞長軍、卞長波、卞長天、卞云勇、卞長雙、衡孝狀均以“沒有盜竊珍貴文物,不能適用刑法第三百二十八條第(四)項的規定”和“犯罪情節較輕,應免予刑事處罰或判處”為由提出上訴。
滁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上訴人卞長軍、卞長波、卞長天、卞云勇、卞長雙、衡孝狀違反國家文物保護法,共同盜掘具有歷史、藝術、文化、科學價值的春秋時代的古墓葬,其行為均已構成盜掘古墓葬罪。鑒于六上訴人均能投案自首,并將挖掘的文物保存完好,主動全部上交,主觀惡性較輕,認罪態度較好,具有悔罪表現,故對六上訴人予以從輕處罰。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九條第(三)項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二十八條、第六十七條第一款、第七十二條和第二十五條第一款之規定,判決如下:
1.維持鳳陽縣人民法院(2007)鳳刑初字第224號刑事判決第一、二、三、四、五、六項中對被告人卞長軍、卞長波、卞長天、卞云勇、卞長雙、衡孝狀的定罪部分;
2.撤銷鳳陽縣人民法院(2007)鳳刑初字第224號刑事判決第一、二、三、四、五、六項中對被告人卞長軍、卞長波、卞長天、卞云勇、卞長雙、衡孝狀的量刑部分;
3.上訴人卞長軍犯盜掘古墓葬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宣告緩刑三年,并處罰金人民幣1萬元;
4.上訴人卞長波犯盜掘古墓葬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宣告緩刑三年,并處罰金人民幣1萬元;
5.上訴人卞長天犯盜掘古墓葬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宣告緩刑三年,并處罰金人民幣1萬元;
6.上訴人卞云勇犯盜掘古墓葬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宣告緩刑三年,并處罰金人民幣1萬元;
7.上訴人卞長雙犯盜掘古墓葬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宣告緩刑三年,并處罰金人民幣1萬元;
8.上訴人衡孝狀犯盜掘古墓葬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宣告緩刑三年,并處罰金人民幣1萬元。
二、主要問題
1.構成盜掘古墓葬罪是否要求行為人明知所盜掘古墓葬具有的歷史、藝術、科學價值?
2.卞長軍等六名被告人的行為能否適用盜掘古墓葬罪中“盜竊珍貴文物”的加重處罰情節?
三、裁判理由
(一)盜掘古墓葬罪要求行為人應當明知所盜掘的是古墓葬,但不要求行為人確切認識到所盜掘古墓葬的歷史、藝術、科學價值。
盜掘古墓葬罪是指違反文物保護法規,私自挖掘具有歷史、藝術、科學價值的古墓葬的行為。盜掘古墓葬罪在主觀方面表現為故意,如果是出于過失行為挖掘了古墓葬,如建筑施工作業中誤挖到古墓葬,則不成立本罪。對于本罪犯罪故意的明知內容的界定,有兩種不同觀點:一種觀點認為,行為人只要明知其盜掘的是古墓葬即可;另一種觀點認為,行為人需明知其盜掘的是具有歷史、藝術、科學價值的古墓葬。
我們贊成前一種觀點,即行為人只要明知其盜掘的是古墓葬即可,主要考慮是:首先,盜掘古墓葬罪的行為人一般不可能確切明知所盜掘古墓葬的歷史、藝術、科學價值。由于古墓葬往往被掩埋于地下,其歷史、藝術、科學價值的鑒定,需要由專業人員借助專門設備作出。即使是專業人員,在古墓葬被完全發掘、其中文物被出土前,也很難對其相關價值作出準確評估。司法實踐中的盜掘者絕大多數是沒有受過專門培訓的非專業人員,他們所具有的認知能力和技術裝備一般不足以使其確切判斷所盜掘古墓葬的歷史、藝術、科學價值。據此,在盜掘之前就要求行為人確切明知所盜掘古墓葬的歷史、藝術、科學價值既不可能也不合理。其次,從司法操作的角度講,如果在訴訟中必須證明行為人明知其所盜掘的是具有歷史、藝術、科學價值的古墓葬,難度較大,不利于對盜掘古墓葬行為的懲治。最后,隨著社會文明的發展和文物基本常識的普及,當前社會一般人對于古墓葬屬于受國家保護、禁止私自挖掘的常識應當均有所明知,也即只要行為人明知了其盜掘的屬于古墓葬,那么就充分了主觀違法性認識要件,且從實際情況看,絕大多數盜掘古墓葬的行為人并不是本著對古墓葬歷史、藝術、科學價值的追求而實施盜掘行為的,他們關心的主要是文物的經濟價值,即他們可能對古墓葬的歷史、藝術、科學價值不甚了解,但一般都認識到古墓葬里“有值錢的東西”。因此,只要行為人明知其盜掘的是古墓葬,就足以反映出其應受懲罰的主觀惡性。
基于以上考慮,我們認為,構成刑法第三百二十八條規定的盜掘古墓葬罪,古墓葬的歷史、藝術、科學價值,不屬于行為人必須主觀認知的內容。只要行為人明知盜掘的對象是古墓葬,即使對該古墓葬的歷史、藝術、科學價值沒有充分認識,且事實上盜掘了具有歷史、藝術、科學價值的古墓葬,就可認定為本罪。
本案六名被告人在板橋鎮古城村北側浙江玻璃廠的施工工地,看見施工的推土機推出了不少古墓葬的青磚和古錢幣,便知道施工工地有古墓葬。六名被告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沒有相關部門批準的情況下,持鐵鍬私自對古墓葬進行了挖掘。雖然國家文物部門對該古墓葬沒有進行保護,但被告人明知自己私自挖掘的是古墓葬,并實施了具體的挖掘行為,而被盜掘的古墓葬經相關部門鑒定確是具有重要的歷史、藝術、科學價值的春秋時期的古墓。六名被告人的盜掘行為客觀上擾亂了國家對古墓葬的管理秩序、侵犯了國家對古墓葬文化遺產的所有權,構成了盜掘古墓葬罪。
(二)本案六被告人的行為不適用“盜竊珍貴文物”的加重處罰情節,應當適用盜掘古墓葬罪基本刑條款。
認定盜掘古墓葬罪的另一個難點在于本罪的客觀行為,即所謂“盜掘”,究竟是要求“既掘又盜”還是只要存在單一的非法挖掘行為即可。我們認為,一般情況下,行為人盜掘古墓葬,就是要從中竊取文物,但不排除在某些情況下,行為人未實際竊得文物。這種情況下,行為人雖未竊走文物,但古墓葬作為一種人類文化遺存,本身就是一種文物,具有一定歷史、藝術、科學價值,盜掘者在未得到許可、不具有專業知識能力、缺少必要設備和保護措施的條件下,擅自挖掘古墓葬,往往會給古墓葬帶來毀滅性的破壞、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失,該行為本身就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因此,并非只有盜得文物才構成盜掘古墓葬罪,“盜掘”之“盜”主要表明了挖掘的非法性,即以非法占有為目的、未經批準的擅自秘密挖掘。盜掘者只要實施了非法挖掘具有歷史、藝術、科學價值的古墓葬的行為,不論是否實際盜得文物,即可構成本罪。
當然,如果盜掘中同時竊取文物,尤其竊取珍貴文物的,將直接導致文物在沒有完善保護措施的情況下出土,往往會進一步造成文物的毀損、流失,這較之單一的盜掘行為危害性更大,應在量刑中加以考慮。刑法第三百二十八條第(四)項規定的“盜掘古文化遺址、古墓葬,并盜竊珍貴文物或者造成珍貴文物嚴重破壞的”即屬于盜掘古墓葬罪的加重量刑情節,應當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并處罰金。認定“盜竊珍貴文物”情節,并不是在私自挖掘古墓葬時挖掘到了珍貴文物,就可適用加重法定情節,同樣必須遵循主客觀相一致的原則。從主觀方面講,行為人必須具有盜竊珍貴文物的故意。這種故意可以是基于對所盜掘古墓葬價值一定認識基礎上的相對明確的故意,至少應當是一種不確定的概括故意,即行為人對結果的具體范圍及其性質沒有確定的認識,而希望、放任這種結果發生的心理態度,簡單說就是“能挖什么是什么,挖了多少算多少”的概括故意。司法實踐中大多數盜掘古墓葬行為人對古墓葬中是否有珍貴文物及具體品級很難形成明確的認知,其所持一般是概括故意。
本案卞長軍等六名被告人盜掘出的青銅編鐘一組為國家一級文物,青銅編鐘一組為國家二級文物,青銅斧、青銅豆為國家三級文物,以上均屬珍貴文物。但綜合本案具體情況分析,對這六名被告人不應適用刑法第三百二十八條第(四)項規定的“盜竊珍貴文物”加重處罰條款,理由主要是:1.被告人主觀上沒有盜竊珍貴文物的意圖。本案案發地點是一個建筑工地,由于施工過程中,挖掘機已經推出古墓的青磚和古錢幣,政府沒有保護,導致當地農民也經常在工地拾找古錢幣,而被告人只是想在工地上私挖古錢幣,對于古錢幣的認識,也是停留在自己留著玩或換一點小錢的想法上,被告人對于挖掘到珍貴文物的客觀事實完全出乎其預料。2.被告人客觀上未實施盜竊珍貴文物的行為。被告人以非法占有古錢幣為目的私自挖掘古墓葬,開始挖掘到粘著泥土的碎罐碎碗,作為文化程度較低的農民,根據其自身素質很難對珍貴文物作出正確的判斷,六名被告人在不知是珍貴文物的情況下,不斷挖掘出青銅器十余件,當挖掘到編鐘時,才意識到這可能是國家保護的文物,在完全有能力繼續挖掘的情況下,馬上停止挖掘并報警上交。該行為也證實被告人確實以較小價值的古錢幣為盜掘目標,對盜竊珍貴文物既不具備明確的故意,也沒有“有什么文物就偷什么文物”的概括故意。值得指出的是,本案中卞長軍等被告人盜掘古墓葬既遂后,在完全有能力繼續挖掘的情況下,主動放棄繼續犯罪,停止挖掘并向公安機關自首、將所挖文物全部主動上交,這與通常盜掘古墓葬既遂后繼續不計后果偷盜文物的行為相比,社會危害性明顯小很多,也反映出被告人的主觀惡性不大,量刑中應酌予從輕處罰。
綜上,卞長軍等被告人以非法占有古錢幣為目的,違反國家文物保護法,私自挖掘具有歷史、藝術、科學價值的春秋時代的古墓葬,其行為構成盜掘古墓葬罪。在盜掘古墓葬的過程中,因對珍貴文物的價值產生錯誤認識,雖然導致了十余件珍貴文物的出土,但不能認定被告人具有“盜竊珍貴文物”的加重處罰情節。二審法院據此改判,對被告人適用盜掘古墓葬罪基本犯的一般條款進行量刑是正確的。
《刑事審判參考》第1130號案例 韓濤、胡如俊盜掘古墓葬案
【摘要】
盜掘古墓葬外的石像生應如何定罪處罰?
構成盜掘古墓葬罪。石像生是古墓葬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歷史、藝術、科學價值;偷挖石像生的行為屬于“盜掘”古墓葬行為;對偷挖石像生的行為不宜以盜竊罪定罪處罰,而應當以盜掘古墓葬罪定罪處罰。
韓濤、胡如俊盜掘古墓葬案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韓濤,男,1981年2月12日生。因涉嫌犯盜掘古墓葬罪于2013年8月9日被逮捕。
被告人胡如俊,男,1982年3月27日生。因涉嫌犯盜掘古墓葬罪于2014年2月27日被逮捕。
江蘇省鎮江市潤州區人民檢察院以被告人韓濤、胡如俊犯盜掘古墓葬罪,向江蘇省鎮江市潤州區人民法院提起公訴。
被告人韓濤、胡如俊對起訴書指控的事實沒有異議,未作辯解。被告人胡如俊的辯護人辯稱:被告人胡如俊系初犯,在共同犯罪中所起作用相對較小,且贓物已被追回,建議法庭對其從輕處罰并適用緩刑。
江蘇省鎮江市潤州區人民法院經審理查明:2007年,被告人韓濤(古玩愛好者)在江蘇省鎮江市南山風景區五風口社區談家灣村口(現鎮江市旅游學校正大門對面)山坡下發現一只石馬(長1.8米,高1.45米,寬0.4米)半埋于地下,根據其經驗判斷該石馬為明清年代用于墓道上的石雕。2012年6月,韓濤與被告人胡如俊經實地調查商議后,于當月的一天晚上,分別聯系吊車、貨車等起重、運輸車輛到達現場,由胡如俊用鐵鍬將覆蓋在石馬周圍的土挖開,把鋼絲繩固定在石馬下,通過吊車將石馬吊裝到貨車上將石馬運走并存放于韓濤事先聯系好的龔恩同經營的鎮江恒達物資回收有限公司院內。2013年7月2日,韓濤通過程敏的聯系,欲將該石馬以5萬—6萬元的價格銷售給他人。當日10時許,韓濤聯系了吊車在鎮江恒達物資回收有限公司院內搬運該石馬時,被公安機關當場抓獲。經鎮江市文物局鑒定,該石馬系放置于墳丘前神道兩側的石像生,為明代三級文物,是明代古墓葬的組成部分。
江蘇省鎮江市潤州區人民法院認為,被告人韓濤、胡如俊共同盜竊具有歷史、藝術、科學價值的古墓葬,其行為均已構成盜掘古墓葬罪,依法應予懲處。韓濤、胡如俊歸案后能夠如實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實,依法可從輕處罰。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韓濤、胡如俊犯盜掘古墓葬罪的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指控的罪名正確,予以采納。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二十八條第一款,第二十五條第一款,第六十七條第三款,第七十二條第一款、第三款,第七十三條第二款、第三款之規定,判處被告人韓濤有期徒刑三年六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三萬元;判處被告人胡如俊有期徒刑三年,緩刑三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二萬五千元。宣判后,被告人韓濤、胡如俊在法定期限內未提出上訴,公訴機關也未提出抗訴,判決已發生法律效力。
二、主要問題
行為人未直接挖掘古墓葬的墓室,而是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偷挖古墓葬墓室以外墓道上的石像生,是否能夠認定為“盜掘古墓葬”行為?
三、裁判理由
本案在審理中,對于被告人偷挖石像生的行為如何定罪有兩種不同觀點:一種觀點認為,被告人的行為不構成盜掘古墓葬罪,只能以盜竊罪論處。盜掘古墓葬罪的犯罪對象僅指古墓葬的墓室,而不包括墓室以外的附屬物,對于墓室以外的附屬物的挖掘不是刑法意義上的“掘”。另一種觀點認為,被告人的行為構成盜掘古墓葬罪。不能狹義地理解“古墓葬”及“掘”的含義,盜掘古墓葬罪的犯罪對象不僅包括古墓葬的主體——墓室,也包括墓室外的一些重要附屬物,如墓道、石像生、碑刻等,對附屬物的偷挖同樣應當認定為刑法意義上的“盜掘”。
我們同意第二種觀點,即對被告人應按照盜掘古墓葬罪定罪處罰,理由如下:
(一)石像生是古墓葬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歷史、藝術、科學價值
盜掘古墓葬罪規定在刑法第六章第四節“妨害文物管理”中,表明盜掘古墓葬罪侵犯的是復雜客體,不僅侵犯了國家對古墓葬的所有權,還侵犯了國家對古墓葬的管理秩序。古墓葬的所有權歸屬于國家,未經批準盜掘古墓葬的行為,無論是否竊得古墓葬中的可移動文物,都是對國家所有權的侵犯。同時,盜掘古墓葬的行為不但會造成文物的嚴重流失,而且使許多文物因缺乏保護而喪失其歷史、藝術、科學價值,有時甚至造成文物的直接毀壞,因而這種行為還侵犯了國家對古墓葬的管理秩序。刑法第三百二十八條對盜掘古墓葬罪規定了三年以上有期徒刑,最高可處無期徒刑的刑罰,只有情節較輕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刑法之所以將盜掘古墓葬罪作為重罪懲處,不僅是為了保護古墓葬的所有權和古墓葬中的珍貴文物,更重要的是古墓葬及其文物中所蘊含的重要歷史、藝術、科學價值。因此,判斷石像生是否是“古墓葬”,不能僅從其是位于墓室內還是墓室外來判斷分析,更應當從本質屬性上分析是否具有古墓葬的重要歷史、藝術和科學價值。
石像生又稱石像、石俑、翁仲,指的是用巨石琢成的仿動物或人物的石像,如古代帝陵神道兩側的石獸、石人等。石像生的設置始于秦漢時期,以后歷代帝王、重臣沿用不衰。石獸有麒麟、獅子、辟邪、龍馬、象、虎、牛、羊、玄鳥等,石人分文、武、勛三臣,以象征文武百官。我國唐乾陵、明孝陵、明十三陵、清東陵、清西陵等均有大型石像生雕塑群。因此,石像生實際已經成為古墓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古墓葬由地上遺跡和地下遺跡組成,古墓葬的墓室、葬具、隨葬品、壁畫、神道、石像生、碑刻、地面建筑等形成一個有機整體,離開了其中任何一部分,古墓葬都是不完整的。因此,上述對象都應當成為盜掘古墓葬罪所要保護的對象。石像生的作用主要是顯示墓主人的身份等級地位,也有驅邪、鎮墓的作用。我國古代墓葬大多是通過隨葬品來判斷墓主人的身份,從明清時代開始,墓葬的墓室內部已經不是主要放置隨葬品了,主要還是通過擺放在外面的一些物品來反映墓主人的身份和地位。石像生一般只有在帝王陵或者等級極高的大臣墓才有,因而相對于其他附屬物而言,石像生具有更高的研究價值。在文物保護手段還不夠成熟、考古發掘還存在一定技術性障礙的情況下,古墓葬附屬物的完整保存對研究一定地區的歷史事件、經濟發展水平、喪葬習俗及民俗等具有重要價值。對那些年代和墓主身份難以認定的古墓,石像生對判明墓主人的身份等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本案中,鎮江市博物館的專家發現現場還有其他墳丘、石刻存在,通過考察查扣的石馬的工藝水平、雕刻方式等,結合證言提到的此前在此曾有石碑刻有“大明開國世公”字樣,在沒有挖掘墓室的情況下,主要根據被偷挖的石馬最終認定這是一處品級很高的明朝開國功臣之墓,對研究鎮江南山風景區的歷史、文化具有極高的價值。由此可見,涉案的石馬完全具有古墓葬所體現出的重要歷史、藝術和科學價值,應當認定為古墓葬。
(二)偷挖石像生的行為屬于“盜掘”古墓葬行為
對于盜掘古墓葬罪中的“盜掘”的含義,實踐中有不同理解。有種觀點認為,“盜掘古墓葬”中的“掘”僅指向下挖掘,通俗地講就是“挖墳掘墓”,是對墓室的開挖,并且通過開挖來達到占有隨葬文物的目的。我們認為這種觀點有失偏頗。從字面上看,“掘”是由“手”和“屈”兩部分組合而成,意為弓著身體用手掏挖,在現代漢語中“掘”是指刨、挖,①即通過清除土的方式實現行為的既定目的。但對刑法語詞的解釋不能僅限于文義解釋。由于我國幅員遼闊,民族眾多,各地的喪葬風俗也各不相同,有土葬、火葬、水葬、塔葬、天葬、樹葬、崖葬等多種,很多墓葬并非位于地面以下,如果將“掘”僅作狹義理解的話,勢必使得刑法保護的古墓葬范圍大大縮小,不利于對散落于全國各地不同種類古墓葬的保護。因此,對什么是刑法上的“盜掘”,不能完全拘泥于“掘”的字面含義,即狹義地理解為“向下挖掘“‘刨開泥土”或者是“在地面以下挖掘”,而應作廣義的理解。
我們認為,從盜掘古墓葬罪所要保護的法益的角度出發,凡是具備以下兩個特征的“破壞性手段”,都可以視為盜掘古墓葬罪的行為方式:(1)行為人秘密實施的行為,旨在破壞古墓葬及其附屬物的完整性或者使其離開原處;(2)行為客觀上破壞了古墓葬及其附屬物所蘊含的歷史、藝術、科學價值。本案被告人偷挖石馬的行為就屬于秘密實施的使古墓葬的附屬物離開原處的行為,符合“盜掘”古墓葬的行為特征。
(三)對偷挖石像生的行為不宜以盜竊罪定罪處罰,而應當以盜掘古墓葬罪定罪處罰
從法理上分析,盜掘古墓葬罪與盜竊罪之間的區別比較明顯:(1)兩罪的主觀方面不同。盜掘古墓葬罪的行為人雖然大多出于獲得墓葬內的珍貴文物高價賣出后牟取暴利的目的,但本罪并未將該目的作為犯罪構成要件,無論出于何種目的,也無論是否實際取得文物,只要行為人實施了盜掘古墓葬的行為都足以成立本罪;而盜竊罪的主觀方面表現為行為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構成犯罪一般以盜竊數額較大、多次盜竊 、入戶盜竊、攜帶兇器盜竊、扒竊等情節為前提。(2)兩罪所侵犯的客體不同。如前所述,盜掘古墓葬罪所侵犯的客體是復雜客體,即國家對古墓葬的所有權和國家對古墓葬的管理秩序;而盜竊罪侵犯的是簡單客體,即公私財產所有權。雖然文物也可以成為盜竊的對象,但不包括尚未脫離古墓葬的文物。(3)兩罪客觀方面不同。盜掘古墓葬罪表現為行為人未經國家有關主管部門批準而擅自挖掘古墓葬的行為;盜竊罪則表現為以秘密竊取的方法,將公私財物轉移到自己的控制之下,并非法占為已有的行為。
在1997年之前,盜掘古墓葬的行為一般以盜竊罪定罪處罰,1997年刑法將盜掘古墓葬罪作為一個單獨的罪名予以規定,旨在加強對具有歷史、藝術、科學價值的古墓葬及其附屬物的保護,故而對盜掘古墓葬罪設置的法定刑明顯重于盜竊罪的法定刑。鑒于盜挖石像生的行為人大多是以轉賣牟利為目的,在多數情況下,可以將盜挖石像生的行為理解為行為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秘密竊取屬于國家所有的文物,這種行為同時構成盜竊罪和盜掘古墓葬罪,屬于想象競合犯。根據想象競合犯“從一重處斷”的原則,應以盜掘古墓葬罪定罪處罰。
另外,從司法實踐來看,如果將盜挖石像生的行為認定為盜掘古墓葬罪,該罪作為行為犯,其定罪標準容易掌握。如果以盜竊罪定罪處罰則會面臨兩個難題:一是盜竊罪必須以竊得文物的數量、等級作為定罪量刑的依據,而實踐中因盜掘行為導致文物毀壞、缺損、滅失而無法進行等級鑒定的比比皆是。二是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盜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的規定,按照等級來定罪量刑的僅限于國有館藏文物,民間文物需要按照評估價格來確定盜竊數額。但實踐中,文物管理部門往往對民間文物只鑒定等級而不鑒定價格,物價部門也往往以無專業知識為由拒絕對文物價格進行鑒定;同時我國文物市場還不健全,文物交易也不夠規范,文物交易價格根據市場行情往往波動較大,因此按照文物的銷贓價格來認定盜竊數額也不夠準確。
綜上,對盜挖石像生的行為以盜掘古墓葬罪定罪處罰既符合法理,又便于司法實踐操作,更有利于對古墓葬的保護。本案被告人韓濤、胡如俊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盜掘屬于國家三級文物的明代古墓葬,原審法院以盜掘古墓葬罪對兩被告人定罪處罰是正確的。
(撰稿:江蘇省鎮江市潤州區人民法院 岳益民 余波 審編:最高人民法院刑四庭 陸建紅)
《刑事審判參考》第1129號案例 謝志喜、曾和平盜掘古文化遺址案
【摘要】
盜掘確定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古文化遺址,但犯罪情節較輕的,如何量刑?
盜掘確定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古文化遺址,犯罪情節較輕,依法決定在法定刑以下判處刑罰的,可以根據犯罪情節、悔罪表現等因素決定是否適用緩刑。
謝志喜、曾和平盜掘古文化遺址案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謝志喜,男,1979年8月26日出生。2012年12月21日被逮捕。
被告人曾和平,男,1978年10月13日出生。2012年12月21日被逮捕。
江西省吉安縣人民檢察院以被告人謝志喜、曾和平犯盜掘古文化遺址罪,向吉安縣人民法院提起公訴。
吉安縣人民法院經公開審理查明:2012年11月15日10時許,被告人謝志喜攜帶手電、手套、不銹鋼碗等工具,前往吉州窯遺址公園,在一個因栽樹形成的地洞內橫向挖掘洞壁,挖了一尺深左右,挖到幾塊帶花紋的碗碎片。當日11時許,被告人曾和平到達現場,進洞后沿著謝志喜挖掘的洞壁繼續深挖。謝志喜、曾和平二人協作將洞壁又掘了一尺余深,挖到了些碎瓷片、一個碎瓶嘴。該地洞位于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吉州窯遺址保護范圍內。
吉安縣人民法院認為,被告人謝志喜、曾和平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違反文物保護法規,擅自在確定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吉州窯遺址保護范圍內挖掘古文物,其行為均已構成盜掘古文化遺址罪。據此,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二十八條第一款.第二十五條第一款之規定,吉安縣人民法院判決如下:
1.被告人謝志喜犯盜掘古文化遺址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年,并處罰金五千元;
2.被告人曾和平犯盜掘古文化遺址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年,并處罰金五千元。
一審宣判后,被告人謝志喜、曾和平不服,向吉安市中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
上訴人謝志喜、曾和平的上訴意見及其辯護人的辯護意見是:二上訴人主觀上不明知該處屬于國家重點保護的古文化遺址范圍內,客觀上也沒有實施挖掘行為,只是在政府搞開發所挖的樹洞內撿碎瓷片,不構成盜掘古文化遺址罪;即使二人的行為構成犯罪,但犯罪情節顯著輕微,社會危害程度不大,應當減輕或者免予處罰。
吉安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上訴人謝志喜、曾和平違反國家文物保護法規,擅自在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吉州窯遺址的保護范圍內挖掘古文物,其行為均已構成盜掘古文化遺址罪。二上訴人提出不知道所挖掘的樹洞處于吉州窯遺址保護范圍內以及沒有挖掘行為的辯解意見與二上訴人在公安機關的供述不符,不予采納;鑒于二上訴人是在政府為綠化而挖的樹洞內盜掘,主觀惡性較小,根據罪刑相適應原則,對二上訴人依法可予以減輕處罰。原判認定事實清楚,證據充分,定罪準確,審判程序合法。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二十八條第一款、第二十五條第一款、第六十三條第二款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五條第一款第二項之規定,吉安市中級人民法院以盜掘古文化遺址罪,分別改判上訴人謝志喜有期徒刑四年,并處罰金五千元;上訴人曾和平有期徒刑三年零六個月,并處罰金五千元。
江西省高級人民法院在復核期間認為,原審上訴人謝志喜、曾和平違反國家文物保護法規,擅自在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江西省吉安縣吉州窯遺址的保護區范圍內挖掘古文物,其行為均已構成盜掘古文化遺址罪。鑒于謝志喜、曾和平是在政府為綠化而挖的樹坑內進行盜掘,盜掘行為亦未給國家重點保護遺址造成嚴重破壞,故其犯罪情節較輕,又有悔罪表現。據此,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六十三條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三百三十六條之規定,裁定撤銷吉安市中級人民法院的刑事判決,發回吉安市中級人民法院重新審判。
吉安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再次審理,以盜掘古文化遺址罪判處謝志喜、曾和平有期徒刑三年,緩刑三年,并處罰金五千元。該判決逐級層報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認為該判決認定的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定罪準確,量刑適當,審判程序合法,裁定予以核準。
二、主要問題
1.在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區域內對政府為栽樹而挖的樹坑進行盜掘的行為是否構成盜掘古文化遺址罪?
2.盜掘確定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古文化遺址,犯罪情節較輕,依法決定在法定刑以下判處刑罰的,可否適用緩刑?
三、裁判理由
(一)在確定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區域內盜掘古文化遺址的行為,依法應當以盜掘古文化遺址罪定罪處罰
古文化遺址、古墓葬,作為人類活動的實物遺存,從不同的側面和領域揭示了一定的歷史現象,體現了我國祖先的思想道德和科學文化水平,其價值和作用是永恒的,是連接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歷史文化紐帶。這些前人給我們留下的珍貴寶藏,不可再生、無法復制,一旦受損則無法挽回。盜掘古文化遺址、古墓葬的違法犯罪活動會使大量未出土的文物脫離特定的環境而失去珍貴的科學價值,也為非法倒賣文物提供了文物源,因此,刑法設立盜掘古文化遺址、古墓葬罪,是保護文物、制止倒賣文物犯罪活動的有效手段。根據刑法第三百二十八條的規定,盜掘具有歷史、藝術、科學價值的古文化遺址、古墓葬的行為,構成盜掘古文化遺址、古墓葬罪。這里的盜掘,是指以出賣或者非法占有為目的,私自秘密挖掘古文化遺址和古墓葬的行為。古文化遺址是指在人類歷史發展中由古代人類創造并留下的表明其文化發展水平的地區,如周口店;古墓葬是指古代(一般指清代以前,含清代)人類將逝者及其生前遺物按一定方式置于特定場所并建造的固定設施。辛亥革命以后,與著名歷史事件有關的名人墓葬、遺址和紀念地,也視同古墓葬、古遺址,受國家保護。對于盜掘古文化遺址罪,一般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分析認定:
1.從主觀方面進行判斷。本罪在主觀上表現為故意,并且以非法出賣或者非法占有為目的。犯罪的故意由認識因素和意志因素組成,對本罪來說,認識因素表現為明知,最重要的是要求行為人明知自己盜掘的是具有歷史、藝術、科學價值的古文化遺址;意志因素表現為希望。由于盜掘古文化遺址罪是以非法出賣或者非法占有為目的的犯罪,因此只能出于直接故意。國家文物主管部門對本案所涉及的江西省吉州窯遺址屬于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已予以立碑公布,被告人謝志喜、曾和平長期生活在當地,憑借其知識、經驗,應當能夠鑒別其挖掘目標的價值。謝志喜供述:“我在吉州窯公園看到一個為栽樹而挖的樹坑里被挖掘機挖出少許碎瓷片,便返回永和鎮購買了一個手電筒,又拿來一雙黃色皮手套和一個鋼碗,于當日來到該樹坑內開始挖掘,與曾和平說好挖到的東西一人一半,我知道所掘位置處于吉州窯遺址范圍內。”曾和平供述:“我前兩天聽說吉州窯作坊后面有碎瓷片撿,遂帶了一個橘紅色的手電筒來到現場,看見謝志喜戴著手套蹲在洞口耙土,謝告訴我已經撿了一些碎瓷片。然后我與謝志喜輪流耙土,誰耙到東西就算誰的。我們知道現場為吉州窯遺址范圍內,想搞些碎片自己玩和賣錢。”從二被告人的供述亦可以看出,二人不僅明知挖掘地屬于吉州窯遺址范圍內,還具有盜掘古文化遺址并非法占有、非法出賣遺址中文物的目的。
2.從客觀方面進行判斷。學界對本罪客觀方面中的“盜掘”是單一行為還是復合行為,即盜掘行為是否包含盜竊文物行為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竊得文物說”認為,本罪客觀方面應當包含實施了挖掘行為并且竊得內藏的物品;“盜掘行為說”認為,只要行為人實施了盜掘行為便構成本罪。我們同意“盜掘行為說”,即只要行為人客觀上實施了挖掘古文化遺址的行為就足以構成本罪。首先,從立法規定來看,刑法第三百二十八條將“盜掘古文化遺址、古墓葬,并盜竊珍貴文物或者造成珍貴文物嚴重損壞”的情形作為本罪的加重處罰情節,而不是規定為犯罪構成要件。其次,在實踐中,有些破壞古文化遺址的案件,盡管情況嚴重,卻未竊得文物或者因文物被毀無法竊取,但對古文化遺址本身的破壞是顯然存在的。可見,是否盜竊珍貴文物或者造成珍貴文物嚴重被破壞,是決定對犯罪分子在哪一個法定刑幅度內量刑的依據,而不是判斷其行為是否構成犯罪的依據。本案中,被告人謝志喜供述其為盜掘文物事先準備挖掘工具,曾和平到達之前其一個人在洞內橫向挖掘洞壁,挖了一尺深左右,挖到幾塊帶花紋的碗碎片。曾和平到達現場進洞后沿著其挖掘的洞壁用手、碼釘繼續深挖,二人協作將洞壁又掘了一尺余深。二被告人挖掘行為持續了一個多小時,對古文化遺址已經造成破壞,客觀上完成了盜掘國家重點保護的古文化遺址的行為。其僅挖到幾塊帶花紋的碗碎片,只是犯罪情節的內容,而不是行為是否構成犯罪的判斷依據。
3.將本罪與盜竊罪區別開來。盜掘古文化遺址罪,是指盜掘具有歷史、藝術、科學價值的古文化遺址的行為。在刑法規定本罪之前,我國法律對于私自挖掘古文化遺址的行為,一般以盜竊罪論處。由于盜掘古文化遺址的犯罪活動猖獗,給國家珍貴歷史文化遺產造成無法估量的損失,從保護文物的角度出發,1991年6月29日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次會議通過了《關于懲治盜掘古文化遺址古墓葬犯罪的補充規定》(已廢止)對刑法補充規定了盜掘古文化遺址罪,由此正式確立了相關保護古文化遺址的罪名、罪狀及嚴厲的法定刑。1997年刑法基本沿用了該補充規定。因此兩罪很容易混淆。兩罪相比較,區別主要在于:首先,侵犯的客體不同。盜掘古文化遺址罪侵犯的客體是復雜客體,即國家對古文化遺址的管理秩序和國家財產所有權;而盜竊罪侵犯的是單一客體,即公私財產所有權。其次,侵犯的對象不同。盜掘古文化遺址罪侵犯的對象是古文化遺址,是不可再生物,一般不能以金額計算,一旦遭到破壞,損失無法挽回;而盜竊罪侵犯的對象為公私財物。最后,客觀表現不同。盜掘古文化遺址罪表現為秘密或者公開地私自掘取行為,不論是否竊得財物,只要實施了盜掘行為就構成該罪。盜掘既不是單純的盜竊,也不是單純的損毀,而是指未經國家文物主管部門批準,私自挖掘,盜掘可謂集盜竊與損毀于一體,其侵害程度相當重。而且,盜掘并不限于挖掘埋藏于地下的古文化遺址、古墓葬,打撈被水淹沒的古文化遺址、古墓葬的,掘出掩埋于其他物體中的古文化遺址、古墓葬的,也應認定為盜掘。而盜竊罪只能表現為秘密竊取公私財物數額較大的行為。
(二)盜掘確定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古文化遺址,犯罪情節較輕,依法決定在法定刑以下判處刑罰的,可以根據犯罪情節、悔罪表現等因素決定是否適用緩刑
根據刑法第三百二十八條第一款規定,只要實施了盜掘具有歷史、藝術、科學價值的古文化遺址、古墓葬行為的,就構成盜掘古文化遺址、古墓葬罪。而盜掘確定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和省級文物保護單位的古文化遺址的,則應當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本案二被告人盜掘確定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古文化遺址的,則應當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的法定刑幅度內處罰。但是,根據本案的具體情節,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處刑罰,并適用緩刑。首先,二被告人有別于有預謀、有準備、攜帶專業挖掘工具流竄作案的專業盜掘文物人員,系臨時起意。二被告人不是刻意去尋找挖掘對象,而是在政府為綠化而挖的樹洞內實施盜掘行為,因而主觀惡性相對較小。其次,二被告人的挖掘持續時間不長,既未給吉州窯遺址造成實質性的嚴重破壞,也未盜得有價值的文物,與采取搗毀、損壞、拆除、焚燒、爆炸等不計后果的破壞性手段盜掘古文化遺址,大肆倒賣、走私文物的犯罪相比,犯罪情節相對較輕。再次,二被告人歸案后均如實供述犯罪事實,且悔罪態度較好。最后,二被告人平時表現較好,無前科劣跡,均系初犯,歸案后認罪悔罪,能夠坦白罪行。綜上,吉安市中級人民法院經綜合評估,認為二被告人的犯罪情節較輕,有悔罪表現,且沒有再犯罪的危險,宣告緩刑對所居住社區沒有重大不良影響,故對被告人謝志喜、曾和平分別以盜掘古文化遺址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緩刑三年,并處罰金五千元,是妥當的。
(撰稿:江西省高級人民法院 王長河 張超平 審編:最高人民法院刑四庭 陸建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