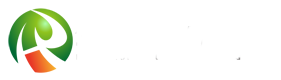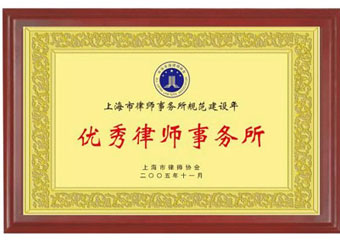上海崇明刑事律師 《解釋》第十條第一款對“犯罪所得”及“犯罪所得產生的收益”的內涵進行了界定。通過犯罪直接得到的贓款、贓物,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條規定的“犯罪所得”。上游犯罪的行為人對犯罪所得進行處理
后得到的孳息、租金等,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條規定的“犯罪所得產生的收益”。
關于“犯罪所得”,“是犯罪直接得到的,既包括通過盜竊、詐騙、搶奪等侵財犯罪獲得之物;也包括通過其他犯罪獲得之物,如偽造、變造的公文、證件等本身經濟價值不大或無法簡單衡量價值的贓物。” 最高人民法院認為:“實踐中,容易出現的爭議是違禁品能否成為贓物?如槍支、彈藥、毒品等能否成為犯罪所得?理論上說,槍支、彈藥及毒品等違禁品也可以成為掩飾、隱瞞的對象,說它們是贓物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是,這些違禁品,我們一般不將其作為普通贓物對待,主要理由有二:一是刑法對掩飾、隱瞞這些違禁品的行為,一般有專門的條文規定,按照特別法優于一般法的原則,應當適用特別規定。二是在司法實踐以及
群眾一般觀念中,違禁品與一般的贓款、贓物是有質的區別,一般的贓款、贓物,除非是有證據證明是贓款、贓物,否則,持有人可以擁有合法的使用權;而違禁品,除非法律特別授權的組織和人員,否則,持有違
禁品本身就是違法甚至犯罪的行為。” “因此,對違禁品進行掩飾、隱瞞的行為,如果我國《刑法》中有相關的規定將其列為獨立的罪名,應以這種獨立的罪名定罪處罰;如果沒有規定,則應當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某些禁止公民隨意持有的物品也可能成為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犯罪對象。例如,對于非法狩獵的普通野生動物,則可以成為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犯罪對象。”
關于“犯罪所得收益”,是以上游犯罪的行為人對犯罪所得進行處理后得到的收益為準。最高人民法院認為:“如果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到了掩飾、隱瞞行為人手上,由此產生的新的收益,則不能認定為犯罪所
得收益的數額。但是,此部分收益雖然不能認定為犯罪數額,仍然是非法所得,應當予以追繳。”此外,“關于將犯罪所得用于投資、經營所獲利潤,是否可認定為犯罪所得收益?這種情況原則上應當認定投資所得
屬于犯罪所得收益。但是,由于這個問題比較復雜,如是否介入合法的勞動投入?如何扣除合法的勞動投入因素?因此,有待于司法實踐的總結,待成熟后再作出相應的規定。但是,如果將犯罪所得進行非法的高利
貸等違法活動而獲得的利益,則應當認定為犯罪所得收益。”

根據1997年刑法,上海崇明刑事律師 構成本罪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或者單處罰金。刑法修正案(六)對本罪增加了一個法定刑幅度,即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旨在嚴厲打擊此類犯罪。但由于司法實踐中對何謂“情節嚴重”沒有明確的標準可循,一方面使得法院輕易不敢認定情節嚴重,不利于打擊嚴重犯罪,另一方面也造成量刑標準不統一,同樣數額、情節的案件在不同地區判決結果差異很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主要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的數額、種類、次數、上游犯罪的性質及對司法機關追查上游犯罪的妨害程度等因素認定“情節嚴重”,規定了一般標準、特殊標準,并設置了兜底條款。關于一般標準。《解釋》從犯罪數額上予以確定,設定為掩飾、隱瞞犯罪所得及其產生的收益價值總額達到十萬元以上。“情節嚴重”的數額標準不宜設置過高,否則實踐中很難用到,但也不宜設置過低,否則可能造成量刑大幅上升,十萬元的數額標準參照了盜竊、詐騙、搶奪刑事案件的有關司法解釋的數額規定,體現了本罪的社會危害性一般要小于上游犯罪的特點。關于特殊標準。包括三種情況:一是掩飾、隱瞞犯罪所得十次以上的,行為次數多,社會危害性大,應嚴厲打擊;二是實施掩飾、隱瞞犯罪所得行為三次以上的,價值總額達到前項十萬元標準的百分之五十(五萬元)的;三是針對公用設備、設施及其他特殊財物,對情節嚴重的標準有所降低,不要求次數的限制,只要數額達到一般標準十萬元的一半即五萬元以上,就可認定為“情節嚴重”。另外,考慮到有的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的行為,雖然所涉及的犯罪數額不大,甚至很小,但上游犯罪的危害特別大,社會影響特別惡劣,甚至給國家和社會帶來巨大的損失,《解釋》規定,“掩飾、隱瞞行為致使上游犯罪無法及時查處,并造成公私財物重大損失無法挽回或其他嚴重后果的”和“實施其他掩飾、隱瞞犯罪所得及其產生的收益行為,嚴重妨害司法機關對上游犯罪予以追究的”的情況下,即使其犯罪數額不到十萬元甚至不到五萬元,仍然應當依法認定為情節嚴重。
| 《關于審理掩飾、隱瞞犯罪所得、 | |